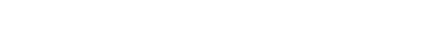师范学院何山石博士在《光明日报》“文学遗产”专栏刊发文章
本网消息 6月24日,《光明日报》在第13版“文学遗产”专版,刊登师范学院何山石博士的文章——《西河诗话》“以民俗说诗”论。

报道链接:https://epaper.gmw.cn/gmrb/html/2024-06/24/nw.D110000gmrb_20240624_3-13.htm
全文如下:
《西河诗话》“以民俗说诗”论
作者:何山石《光明日报》(2024年06月24日13版)
清初学人毛奇龄,字大可,世称“西河先生”。毛奇龄著述宏富,以选书严苛闻名的《四库全书》,录其著述达数十种之多,足见其在清代学术地位之重要。《西河诗话》共八卷,是体系庞大的毛氏著述中非常重要的一种,集中体现了毛奇龄在诗的解释方式、说诗与考据的关系、论诗评诗策略等方面的观念。若细读《西河诗话》,明显能感受到:毛奇龄说诗论诗,非常关注诗与民俗的共生关系,喜从“民俗”着眼,采取“以民俗说诗”的论诗策略,这成为《西河诗话》不同于其他诗话著述的重要特征。
诗话须解决“诗俗共生”命题
中国古典诗歌创作,一直有着采俗入诗的传统,民俗与诗歌共生的源头,可以推溯至《诗经》时代的民间歌谣采集活动。现在,普遍能为人接受的观点,就是《诗经》“国风”中的诗歌,就是借助当时的采诗制度,将民间歌谣采集后汇聚而成。但当中国古代诗歌获得长足发展之后,诗歌与民俗的关系,很快就不再单纯是采集民间歌谣这样的民俗材料这般简单了,而是慢慢变成诗人在创作诗歌时,将多样的民俗材料引入自己的歌唱中。
如此一来,对诗歌进行解释、评论时,要准确理解诗意,准确评品诗作,说诗者就必须要随时准备说清楚诗中包含的民俗现象,不然不可以论诗。《西河诗话》中就有其例,如卷一第九则:“予过西昌萧孟昉于长干佛寺,适句容张芳、余杭吴山涛在坐。主人出沤蓝菜说饼,坐中共作说沤蓝饼诗。第沤蓝无考,或作‘吴蓝’,或作‘瓯蓝’,俱无所据。其菜味苦,而涤淘之,香鲜异常。唯秣陵高坐寺中产此物,他处不产。或云:高坐上人从西方得此种。又云:明初黔国征南时,取之西洋[①]中。又云:海中有沤蓝国献此。不知孰是。”此处,毛奇龄对“沤蓝菜”这一地方风物,既以之为题材,形诸歌咏;又花费大量笔墨,来对这一风物进行考证,虽然苦索而无定论,但各种猜测,如从西方得种、取之西洋[①]中、沤蓝国所献,都是力图考证清楚这一风物,为后来的读者提供理解的方便。而同时,这一考证过程,又与民间传说、民间神话相关联,这又是在用民俗来考证“沤蓝菜”这一风物,正可视为以俗证俗。
再以钱钟书的一则风物考证来作为说明。钱钟书在《谈艺录》第二则“论黄山谷诗”的“春网荐琴高”之句时,指出任渊所注“琴高”为“鲤鱼”是错误的,他援引赵与时《宾退录》所载为证:“今宁国府泾县东北,有琴溪,俗传琴高隐处。有小鱼,他处所无,号琴高鱼。岁三月,数十万一日来集,网取盐曝;州县苞苴,索为土宜。旧亦入贡,乾道间始罢。前辈多形之赋咏,……蜀人任渊注山谷时,不知土宜,但引《列仙传》,直云鲤鱼,误矣。”“琴高”原是土宜风物,而且,这一风物还关联着民间故事等民俗现象。如果不能正确解释何为“琴高”,则对黄庭坚诗句的理解就一定是不完整的。
所以,作为中国古典诗歌评论的主要载体的“诗话”,如果不能圆满解决“诗俗共生”这一释诗难题,那说诗效果一定不尽如人意,甚或成为千古笑柄。
毛奇龄“以俗说诗”的维度
大略而言,《西河诗话》中涉及的民俗现象,包括传说、故事、风物、杂技、戏曲、舞蹈、说梦、笑话、俗语、民间俗信、民歌、异俗等,毛奇龄自如地调动这些民俗资源,以为说诗之具。
在《西河诗话》中,毛奇龄“民俗说诗”的策略,基本在三重维度上展开:其一,解释、考证所论诗句中涉及的民俗现象;其二,用民俗来形象地对诗作进行评价、品评;其三,对某些民俗现象进行专门的记录。
第一重维度,又有两层含意:一是解释所品评的诗句中包含着何种民俗,二是用诗句来说明、解释某种民俗。于第一层含意,如《西河诗话》卷六第十三则:“京师祈雨,有诵《塞外祈雨》诗者云:‘龙女携云出,雷鞭击浪游。晴天张雨伞,炎日覆旃裘。’相传奉天俗,官府步祷,则凡路两傍士女,倚墙泼水,不顾官府,以为得雨之兆,故祷者必旃裘雨伞以障水。”毛奇龄就对《塞外祈雨》诗中包含的祈雨民俗,以奉天地区的风俗为例,进行了说明。于第二层含意,如《西河诗话》卷五第一则:“今上尝出塞驻跸乌兰布尔哈酥,有以道傍紫花献者,不得其名,然蓓蕾蕤纚可爱。询之,士人曰:‘此长十八也。’按高侍讲《松亭行纪》载元葛逻禄乃贤《塞上曲》云:‘双鬟小女玉娟娟,自卷毡帘出帐前。忽见一枝长十八,折来簪在帽檐边。’则知其名旧矣。”对于“长十八”这一地域特征极浓的植物,也一样可以当成地方风宜土物来看待,毛奇龄便征引诗句来说明这一风物。
第二重维度,用民俗来形象地对诗作进行评价,这是毛奇龄“以俗说诗”的大端。毛氏对诗的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、对诗人的品评,很多时候都借助民俗来形象说明,如诗的雅、俗问题,《西河诗话》卷五中言:“诗以雅见难,若裸私布秽,则狂夫能之矣;亦以涵蕴见难,若反唇戛膊,则市牙能之矣;又以不著厓际见难,若搬楦头、翻锅底,则呆儿能之矣。然则为宋诗者,亦何难、何能、何才技,而以此夸人,吾不解也。”毛奇龄不仅指出,诗以雅正、含蓄蕴藉、不露痕迹为高,而且,为了说明这一点,他使用了“俗”的手法,诸如狂夫、市牙都是“俗”味说法,“搬楦头”“翻锅底”等更是民间俗语,来说明诗歌过于直露的毛病,形象生动。
第三重维度,是毛奇龄在《西河诗话》中,仅仅记述某些民俗现象,甚至完全不涉及说诗这一主题,这一点使《西河诗话》显得更为独特。如卷一第十七则:“秣陵周雪客饮,席有陈道人在坐,请为幻术,取萁秆及菼,吹之出火,引扇邀月栖壁,一切射藏发覆,揭之如睹,且能使握松相博,彼我互易。时客有谓五金不能易者,雪客取金二,令纪伯紫、方邵村分握之,道人呼曰:‘过!’忽伯紫手中觉金从虎口拔去,而邵村食指隙内有物纳入,及开掌而彼金已移此矣。后道人避席,席中各书纸阄,杂和之令射。道人至,手抡其阄,各认取分还,然后亦书纸,与阄并发,悉吻合。唯至姜定庵阄,咨嗟曰:‘此三字难射,当是一鳞虫名否?’定庵私喜,以为必失,盖其中本‘花龛’二字也。及书发,曰:‘花合龙。’其巧如此。时有诗记之,见《罗村集》。”此则中,毛奇龄所津津乐道的,完全集中于幻术(即魔术)、射覆这样的民间杂耍、民间游戏等民俗现象上。毛奇龄似乎忘记了自己写的是诗话,他已经完全偏离了说诗,仅在末尾以“有诗记之”几字提及,一笔带过。
“嗜俗”原因及诗话意义
毛奇龄“嗜俗”,喜欢在论诗谈艺中织入民俗,之中的原因也值得探究。
首先,毛奇龄对民俗的价值体认,一直延续着“观风问俗”、以风俗观治乱的传统理念。历代知识分子,特别是如毛奇龄这样的仕宦之人,对民俗极为关注,因为他们坚信,有良俗,才有良治,风衰俗败,一定关联着政毁人亡。出仕为官之人,如果有治理好一方百姓的抱负,不仅会关注治理辖地的民情风俗,保护好有利于地方治理的民俗,而且会不遗余力推动新的良善民俗的培育、生长,以便构筑出理想中的良俗公序,形成俗美人和的治理局面。
其次,毛奇龄在学问上炫博逞才的疏狂气质,也让他喜欢借助民俗来舒洒才情。《四库总目提要》评价《西河诗话》时这样说:“毛氏性疏狂,论诗扬唐抑宋,多出己意,不免失据。然精于韵学,故与诗学亦自不隔,论诗乐关系等尤有可听,与王士禛、赵执信等专研古诗声调者又自不同。又以经历广泛,曾任职史馆,其笔亦擅状物记事,上自宫闱秘阁,下及市俗名物之牵系于诗者,随所闻见,信笔书来,颇存明末清初坛坫之状貌。”所以,毛奇龄是出于对自己学养的自信,才选择“以民俗说诗”的路子。
再次,诗话中使用民俗资源来说诗,往往有意想不到的解释效果。正如钱钟书在《七缀集》中所说的:“倒是诗、词、随笔里,小说、戏曲里,乃至谣谚和训诂里,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,说出了精辟的见解,益人神智;把它们演绎出来,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。”钱钟书就认为,“先学无情后学戏”这句谚语,比狄德罗的《葡京国际官网戏剧演员的诡论》以及一大批研究者论述的“演员必须自己内心冷静,才能惟妙惟肖地体现所扮角色的热烈情感”要明白晓畅得多。毛奇龄在说诗中如此看重民俗,也是因为他在解决诗格、诗识、诗才、诗与经、雅与俗等诸多重要的说诗命题时,能一语中的,直击问题的要害。